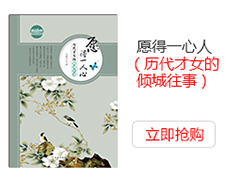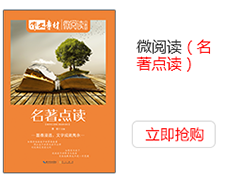吴念真:掌握世俗秘密的人
作者:
匿名
分类:
精品阅读
子类:
读点经典
吴念真,1952年生于台北县,在台湾文化界,吴念真被人们称作“全方位文化创意人”。他被认为是“掌握世俗秘密的人”:敏感、细腻。于别人而言,这是生命中的“负担”,但吴念真认为说好故事可以先感动作者,再感动别人,他的文字总会在不经意间直指人心。“找到小小的喜悦认真地活着吧”,就好比那暗黑世界里的微光。
佳作欣赏
思 念
吴念真
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好像很喜欢邻座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常常提起她。每次一讲到她的种种琐事时,你都可以看到他眼睛发亮,开心到藏不住笑容的样子。
他的爸妈都不忍说破,因为他们知道不经意的玩笑都可能给这年纪的孩子带来巨大的羞怒,甚至因而阻断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对异性那么单纯而洁净的思慕。
双方家长在校庆时孩子们的表演场合里见了面;女孩的妈妈说女儿常常提起男孩的名字,而他们也一样有默契,从不说破。
女孩气管不好,常咳嗽感冒,老师有一天在联络簿上写说:邻座的女生感冒了,只要她一咳嗽,孩子就皱着眉头盯着她看,问他说是不是咳嗽的声音让你觉得烦?没想到孩子却说:不是,她咳得好辛苦哦,我好想替她咳!
老师最后写道:我觉得好丢脸,竟然用大人这么自私的想法去污蔑一个孩子那么善良的心意。
爸妈喜欢听他讲那女孩子点点滴滴,因为从他的描述里仿佛也看到了孩子们那么自在、无邪的互动。
“我知道为什么她写的字那么小,我写的那么大,因为她的手好小,小到我可以把它整个包——起来哦!”
爸妈于是想着孩子们细嫩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样子,以及他们当时的笑容。
“她的耳朵有长毛耶,亮晶晶的,好好玩!”
爸妈知道,那是下午的阳光照进教室,照在女孩的身上,女孩耳轮上的汗毛逆着光线于是清晰可见;孩子简单的描述中,其实有无比深情的凝视。
三年级上学期的某一天,女孩的妈妈打电话来,说他们要移民去加拿大。
“我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有遗憾……”女孩的妈妈说,“如果有,我会觉得好罪过……”
没想到孩子的反应倒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平淡。
有一天下课后,孩子连书包也没放就直接冲进书房,搬下世界旅游的画册便坐在地板上翻阅起来。
爸爸问他说:你在找什么?孩子头也不抬地说:我在找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什么,因为xx她们要搬家去那里!
画册没翻几页,孩子忽然就大笑起来,然后跑去客厅抓起电话打,拨号的时候还是一边忍不住地笑;之后爸爸听见他跟电话那一段的女孩说:你知道多伦多附近有什么吗?哈哈,有破布耶……真的,书上写的,你听哦……“你家那块破布是世界最大的破布”,哈哈哈……骗你的啦……它是说尼加拉瓜瀑布是世界最大的瀑布啦……哈哈哈……
孩子要是有遗憾、有不舍,爸妈心里有准备,他们知道唯一能做的事叫“陪伴”。
后来女孩走了,孩子的日子寻常过,和那女孩相关的连结好像只有他书桌上那张女孩的妈妈手写的英文地址。
寒假前一个冬阳温润的黄昏,放学的孩子从巴士下来时神情和姿态都有点奇怪。他满脸通红,眼睛发亮,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好像捏着什么无形的东西,快步地跑向在门口等候的爸爸。
“爸爸,她的头发耶!”孩子一走近便把右手朝爸爸的脸靠近,说,“你看,是xx的头发耶!”
这时爸爸才清楚地看到孩子两指之间捏着的是两三条长长的发丝。
“我们大扫除,椅子都要翻上来……我看到木头缝里有头发……”孩子讲得既兴奋又急促,“一定是xx以前夹到的,你说是不是?”
“你……要留下来做纪念吗?”爸爸问。
孩子忽然安静下来,然后用力地、不断地摇着头,但爸爸看到他的眼睛慢慢冒出不知忍了多久的眼泪。他用力地抱着爸爸的腰,把脸贴在爸爸的胸口上,忘情地号啕大哭起来,而手指依然紧捏着那几条正映着夕阳的余光在微风里轻轻飘动的发丝。
(摘自《这些人,那些事》一书,译林出版社)
寂寞
吴念真
阿照跟她的爸爸一点都不亲,就连“爸爸”似乎也没叫过几次。
这个爸爸其实是她的继父。妈妈在她四岁的时候离了婚,把阿照托给外婆照顾,自己跑去北部谋生。
阿照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带了一个男人来,说是她的新爸爸;不过,她不记得那时候是否叫过他,记得的反而是那男人给了她一个红包,以及她从此改了姓。
改姓的事被同学问到气、问到烦,所以这个爸爸对她来说不仅陌生,甚至从来都没好感。一直到国中三年级,阿照才被妈妈从外婆家带到北部“团圆”,而且听说这还是那男人的建议,说以后如果要考上好大学,她应该到北部来读高中。那时候妈妈和那男人生的弟弟都已经上小学了。
男人在工厂当警卫,有时日班有时夜班,妈妈则在同一家工厂帮员工办伙食,早出晚归,一家人始终没交集,各过各的。不久之后,阿照考上台北的高中,租房子自己住,即便假日也很少回去。
外婆在阿照大三那年过世,不过,之后的寒暑假,阿照也同样很少回家。她给自己的理由是要打工、读书、谈恋爱,其实自己清楚真正的原因是对那个家根本一点感情也没有。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儿子太不成材还是怎样,那男人对待两个孩子有很明显的差别待遇,比如跟儿子讲话总是粗声粗气,对阿照则和颜悦色,过年给的红包永远阿照的比较厚,儿子只要稍微嘟囔一声,他就会大声说:“你平常拿的、偷的难道还不够多?”
阿照大学毕业申请到美国学校的那年他从工厂退休,妈妈原本希望阿照先上班赚到钱才出国,没想到他反而鼓励她说念书就要趁年轻。阿照记得那天她跟他说:“爸爸,谢谢!”不过,才一说出口就觉得自己可耻,因为在这之前她不记得是否曾经这么叫过他。
从美国回来后,阿照在外商公司做事。弟弟在她出国的那几年好像出了什么事,偷渡到大陆之后音讯全无,连几年前妈妈胰脏癌过世都没回来。孤孤单单的爸爸也没给阿照增加什么负担,他把房子卖了,钱交给阿照帮他管理,自己住到老人公寓去。
阿照也一直单身,所以之后几年的假日,他们见面、聊天的次数和时间反而比以前多很多。有一天阿照去看他,他不在,阿照出了大门才看到他坐出租车回来,说是去参加一个军中朋友的葬礼。阿照陪他走回房间的路上他一直沉默着,最后才跟阿照说可不可以帮他买一个简单的相机,说他想帮几个朋友拍照,理由是:“今天老宋那张遗照真不象样!”后来阿照帮他买了。
去年冬天他过世了。阿照去整理他的遗物,东西不多,其中有一个大纸盒,阿照发现里头装着的是一大叠放大的照片和她买的那部照相机。相机还很新,也许用的次数不多,更也许是他保护得好,因为不仅原装的纸盒都还在,里头还塞满干燥剂并且罩上一个塑料套。
至于那些照片拍的应该都是他的朋友,都老了,背景有山边果园,有门口,有小巷,也有布满鹅卵石的东部海边,不过每个人还都挺合作,都朝着镜头笑,就连一个躺在病床上插着鼻胃管的老伯伯也一样,甚至还伸出长满老人斑的手臂用弯曲的手指勉强比了一个“V”。
阿照一边看一边想象着他为了拍这些照片所有可能经历过的孤单的旅程,想象他独自坐在火车或公路车上的身影,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踯躅的样子,他和他们可能吃过的东西、喝过的酒、讲过的话以及最后告别时可能的心情。
当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阿照先是惊愕,接着便是无法抑制的号啕大哭。照片应该是用自动模式拍的,他把妈妈、弟弟、还有阿照留在家里的照片,都拿去翻照、放大、加框,然后全部摆在一张桌子上,而他就坐后面用手环抱着那三个相框朝着镜头笑。
照片下边就像早年那些老照片的形式一般印上了一行字,写着:“魏家阖府团圆,民国九十八年秋。”阿照说,那时候她才了解那个男人那么深沉而无言的寂寞。
(摘自《羊城晚报》2012年8月26日)
吴念真语录
生命里某些当时充满怨怼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这些人、那些事在经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都只剩下笑与泪与感动和温暖。
——《这些人,那些事》
我们要飞到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遥远的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光亮。
——《张三的歌》
往事何必转头看,将伊当作梦一般。
——《桂花巷》
人生很多滋味都要到一个年纪才能懂得去细细品味,比如类似这种相濡以沫的感动和幸福,然而当你一旦懂了,一起却都已经远了。
——《特别的一天》
作家印象
吴念真——掌握世俗秘密的人
赵瑜
在电影《一一》里,吴念真饰演的“NJ”遇到了一个早些年的恋人,我确信我也在《这些人,那些事》中遇到了她,应该是《情书》中的“她”。不只是她,还有影片中的弟弟,应该也是《遗书》中的弟弟。
曾经被人戏称为“吴金马”的吴念真,五次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自然,他的剧本里满是他自己的气息。所以,多数看过杨德昌电影《一一》或侯孝贤电影《恋恋风尘》的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吴念真”情结。其实,这种情结是一种“中年情怀”,一切坚硬的事物过了三十岁便开始融化。那些激情随着时间慢慢消蚀,多数梦想都挤压在时间的储藏盒里,成为失效的药丸。
吴念真有悲悯情怀,这缘自他幼年时的苦难史。那种植入身体的记忆像一味沾满了蚯蚓腥味的药引子,每一次生病或者伤怀时,都会自然而然地从内心里跃出。
我喜欢吴念真认识的这些人,不论是幼小时的邻居,兵营时的战友,以及年长以后的人事。这些人,分别活在他的记忆里,或者一封信里,或者一张旧照片里,又或是活在家乡的某块稻田里、某棵树下。只要是吴念真路过那里,翻开那些书信,便会打开自己的过往。
那些事,分别活在吴念真身边人的口述里。吴念真从小学时起开始代人写信,那些家常里短的事情,别人口述梗概由他来丰润,这正是一个作家的基础训练。我相信,自他成功地给人代写第一封信开始,他已经注定是一个作家。写作,难道不就是将一个人饱含着苦痛的秘密一点点摊开,加进糖分,中和人世间的灰暗,照亮别人和自己。
吴念真是一个有磁场的人,他畏惧自己有过的一切机缘。在《这些人,那些事》的序言里,他写了四个算命的人对他人生的预测,那种将生命中未知的领域交给一个陌生人来排序的信任,其实是对未知生活的畏惧。想借着别人的提醒,来避开不必要的沉重。
他不是一个被恩宠过的孩子,幼小时的记忆是贫穷和尴尬。在《只想和你接近》中,给受伤的父亲剪完指甲后,作为奖励,父亲领他看的电影竟然在他的脑子里储存了二十年。而电影《恋恋风尘》中,醉酒后的父亲给“阿远”的那块手表,也是对吴念真自己生活的抄袭。《心意》里写到的那支“俾斯麦”牌钢笔,就是父亲醉酒后仍然没忘记买给他的礼物。
村庄里的人真的很多,让我们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赞美吴念真有写作才华的,竟然是将吴念真父亲抓去派出所的警察。这个驻在他们村子里的警察很胖,当时吴念真的父亲喜欢赌钱,赌得昏天暗地,不顾家里。吴念真将此事写到了日记里,被老师看到,老师建议吴念真写一封信来举报自己的父亲。可以想象吴念真写这封信的情景,我想到了张爱玲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用英文写信给报馆,骂自己父亲的情景。写信的结果,除了换来信的曝光率(村子里大多数人都来参观这封举报信)以外,还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吊起来打了一顿。而关于这个警察的模样,吴念真写到了电影《多桑》的剧本里。直到多年以后,吴念真出名,那警察还记着他。
这些人还有很多,整天嘻嘻哈哈从不调皮捣蛋的傻子阿荣,最后却成了抢劫犯;给弟弟买大一号衣服的阿旺;背九九乘法表的老鼠仔;做过妓女,偷偷来求吴念真给她的哥哥写信借钱的阿英;帮着吴念真和战友小包证明清白的店铺女孩阿媛;只是孤独得厉害在深夜抱了一个女孩便被抓到监狱里的“强奸未遂犯”……
这些普通的人,或温暖,或滞重,或忧伤,或单纯,却一个个泛着尘世的体温,让我们在合上书本的瞬间,湿润眼睛。有一个读者在赞美吴念真的时候,说,我最讨厌煽情,可是,却在读吴念真的时候泪流满面。
越是简单内敛的感情,越容易产生共鸣。吴念真的文章像极了一曲舒缓又温暖的钢琴曲,中间有转折的音符,将我们共同的记忆打开。翻开这些日常的人和事,我觉得像进入了一个储满秘密的地下室,而吴念真正是配钥匙的那个人。
(摘自《南岛视界》2014年第5期)
佳作欣赏
思 念
吴念真
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好像很喜欢邻座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常常提起她。每次一讲到她的种种琐事时,你都可以看到他眼睛发亮,开心到藏不住笑容的样子。
他的爸妈都不忍说破,因为他们知道不经意的玩笑都可能给这年纪的孩子带来巨大的羞怒,甚至因而阻断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对异性那么单纯而洁净的思慕。
双方家长在校庆时孩子们的表演场合里见了面;女孩的妈妈说女儿常常提起男孩的名字,而他们也一样有默契,从不说破。
女孩气管不好,常咳嗽感冒,老师有一天在联络簿上写说:邻座的女生感冒了,只要她一咳嗽,孩子就皱着眉头盯着她看,问他说是不是咳嗽的声音让你觉得烦?没想到孩子却说:不是,她咳得好辛苦哦,我好想替她咳!
老师最后写道:我觉得好丢脸,竟然用大人这么自私的想法去污蔑一个孩子那么善良的心意。
爸妈喜欢听他讲那女孩子点点滴滴,因为从他的描述里仿佛也看到了孩子们那么自在、无邪的互动。
“我知道为什么她写的字那么小,我写的那么大,因为她的手好小,小到我可以把它整个包——起来哦!”
爸妈于是想着孩子们细嫩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样子,以及他们当时的笑容。
“她的耳朵有长毛耶,亮晶晶的,好好玩!”
爸妈知道,那是下午的阳光照进教室,照在女孩的身上,女孩耳轮上的汗毛逆着光线于是清晰可见;孩子简单的描述中,其实有无比深情的凝视。
三年级上学期的某一天,女孩的妈妈打电话来,说他们要移民去加拿大。
“我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有遗憾……”女孩的妈妈说,“如果有,我会觉得好罪过……”
没想到孩子的反应倒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平淡。
有一天下课后,孩子连书包也没放就直接冲进书房,搬下世界旅游的画册便坐在地板上翻阅起来。
爸爸问他说:你在找什么?孩子头也不抬地说:我在找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什么,因为xx她们要搬家去那里!
画册没翻几页,孩子忽然就大笑起来,然后跑去客厅抓起电话打,拨号的时候还是一边忍不住地笑;之后爸爸听见他跟电话那一段的女孩说:你知道多伦多附近有什么吗?哈哈,有破布耶……真的,书上写的,你听哦……“你家那块破布是世界最大的破布”,哈哈哈……骗你的啦……它是说尼加拉瓜瀑布是世界最大的瀑布啦……哈哈哈……
孩子要是有遗憾、有不舍,爸妈心里有准备,他们知道唯一能做的事叫“陪伴”。
后来女孩走了,孩子的日子寻常过,和那女孩相关的连结好像只有他书桌上那张女孩的妈妈手写的英文地址。
寒假前一个冬阳温润的黄昏,放学的孩子从巴士下来时神情和姿态都有点奇怪。他满脸通红,眼睛发亮,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好像捏着什么无形的东西,快步地跑向在门口等候的爸爸。
“爸爸,她的头发耶!”孩子一走近便把右手朝爸爸的脸靠近,说,“你看,是xx的头发耶!”
这时爸爸才清楚地看到孩子两指之间捏着的是两三条长长的发丝。
“我们大扫除,椅子都要翻上来……我看到木头缝里有头发……”孩子讲得既兴奋又急促,“一定是xx以前夹到的,你说是不是?”
“你……要留下来做纪念吗?”爸爸问。
孩子忽然安静下来,然后用力地、不断地摇着头,但爸爸看到他的眼睛慢慢冒出不知忍了多久的眼泪。他用力地抱着爸爸的腰,把脸贴在爸爸的胸口上,忘情地号啕大哭起来,而手指依然紧捏着那几条正映着夕阳的余光在微风里轻轻飘动的发丝。
(摘自《这些人,那些事》一书,译林出版社)
寂寞
吴念真
阿照跟她的爸爸一点都不亲,就连“爸爸”似乎也没叫过几次。
这个爸爸其实是她的继父。妈妈在她四岁的时候离了婚,把阿照托给外婆照顾,自己跑去北部谋生。
阿照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带了一个男人来,说是她的新爸爸;不过,她不记得那时候是否叫过他,记得的反而是那男人给了她一个红包,以及她从此改了姓。
改姓的事被同学问到气、问到烦,所以这个爸爸对她来说不仅陌生,甚至从来都没好感。一直到国中三年级,阿照才被妈妈从外婆家带到北部“团圆”,而且听说这还是那男人的建议,说以后如果要考上好大学,她应该到北部来读高中。那时候妈妈和那男人生的弟弟都已经上小学了。
男人在工厂当警卫,有时日班有时夜班,妈妈则在同一家工厂帮员工办伙食,早出晚归,一家人始终没交集,各过各的。不久之后,阿照考上台北的高中,租房子自己住,即便假日也很少回去。
外婆在阿照大三那年过世,不过,之后的寒暑假,阿照也同样很少回家。她给自己的理由是要打工、读书、谈恋爱,其实自己清楚真正的原因是对那个家根本一点感情也没有。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儿子太不成材还是怎样,那男人对待两个孩子有很明显的差别待遇,比如跟儿子讲话总是粗声粗气,对阿照则和颜悦色,过年给的红包永远阿照的比较厚,儿子只要稍微嘟囔一声,他就会大声说:“你平常拿的、偷的难道还不够多?”
阿照大学毕业申请到美国学校的那年他从工厂退休,妈妈原本希望阿照先上班赚到钱才出国,没想到他反而鼓励她说念书就要趁年轻。阿照记得那天她跟他说:“爸爸,谢谢!”不过,才一说出口就觉得自己可耻,因为在这之前她不记得是否曾经这么叫过他。
从美国回来后,阿照在外商公司做事。弟弟在她出国的那几年好像出了什么事,偷渡到大陆之后音讯全无,连几年前妈妈胰脏癌过世都没回来。孤孤单单的爸爸也没给阿照增加什么负担,他把房子卖了,钱交给阿照帮他管理,自己住到老人公寓去。
阿照也一直单身,所以之后几年的假日,他们见面、聊天的次数和时间反而比以前多很多。有一天阿照去看他,他不在,阿照出了大门才看到他坐出租车回来,说是去参加一个军中朋友的葬礼。阿照陪他走回房间的路上他一直沉默着,最后才跟阿照说可不可以帮他买一个简单的相机,说他想帮几个朋友拍照,理由是:“今天老宋那张遗照真不象样!”后来阿照帮他买了。
去年冬天他过世了。阿照去整理他的遗物,东西不多,其中有一个大纸盒,阿照发现里头装着的是一大叠放大的照片和她买的那部照相机。相机还很新,也许用的次数不多,更也许是他保护得好,因为不仅原装的纸盒都还在,里头还塞满干燥剂并且罩上一个塑料套。
至于那些照片拍的应该都是他的朋友,都老了,背景有山边果园,有门口,有小巷,也有布满鹅卵石的东部海边,不过每个人还都挺合作,都朝着镜头笑,就连一个躺在病床上插着鼻胃管的老伯伯也一样,甚至还伸出长满老人斑的手臂用弯曲的手指勉强比了一个“V”。
阿照一边看一边想象着他为了拍这些照片所有可能经历过的孤单的旅程,想象他独自坐在火车或公路车上的身影,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踯躅的样子,他和他们可能吃过的东西、喝过的酒、讲过的话以及最后告别时可能的心情。
当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阿照先是惊愕,接着便是无法抑制的号啕大哭。照片应该是用自动模式拍的,他把妈妈、弟弟、还有阿照留在家里的照片,都拿去翻照、放大、加框,然后全部摆在一张桌子上,而他就坐后面用手环抱着那三个相框朝着镜头笑。
照片下边就像早年那些老照片的形式一般印上了一行字,写着:“魏家阖府团圆,民国九十八年秋。”阿照说,那时候她才了解那个男人那么深沉而无言的寂寞。
(摘自《羊城晚报》2012年8月26日)
吴念真语录
生命里某些当时充满怨怼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这些人、那些事在经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都只剩下笑与泪与感动和温暖。
——《这些人,那些事》
我们要飞到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遥远的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光亮。
——《张三的歌》
往事何必转头看,将伊当作梦一般。
——《桂花巷》
人生很多滋味都要到一个年纪才能懂得去细细品味,比如类似这种相濡以沫的感动和幸福,然而当你一旦懂了,一起却都已经远了。
——《特别的一天》
作家印象
吴念真——掌握世俗秘密的人
赵瑜
在电影《一一》里,吴念真饰演的“NJ”遇到了一个早些年的恋人,我确信我也在《这些人,那些事》中遇到了她,应该是《情书》中的“她”。不只是她,还有影片中的弟弟,应该也是《遗书》中的弟弟。
曾经被人戏称为“吴金马”的吴念真,五次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自然,他的剧本里满是他自己的气息。所以,多数看过杨德昌电影《一一》或侯孝贤电影《恋恋风尘》的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吴念真”情结。其实,这种情结是一种“中年情怀”,一切坚硬的事物过了三十岁便开始融化。那些激情随着时间慢慢消蚀,多数梦想都挤压在时间的储藏盒里,成为失效的药丸。
吴念真有悲悯情怀,这缘自他幼年时的苦难史。那种植入身体的记忆像一味沾满了蚯蚓腥味的药引子,每一次生病或者伤怀时,都会自然而然地从内心里跃出。
我喜欢吴念真认识的这些人,不论是幼小时的邻居,兵营时的战友,以及年长以后的人事。这些人,分别活在他的记忆里,或者一封信里,或者一张旧照片里,又或是活在家乡的某块稻田里、某棵树下。只要是吴念真路过那里,翻开那些书信,便会打开自己的过往。
那些事,分别活在吴念真身边人的口述里。吴念真从小学时起开始代人写信,那些家常里短的事情,别人口述梗概由他来丰润,这正是一个作家的基础训练。我相信,自他成功地给人代写第一封信开始,他已经注定是一个作家。写作,难道不就是将一个人饱含着苦痛的秘密一点点摊开,加进糖分,中和人世间的灰暗,照亮别人和自己。
吴念真是一个有磁场的人,他畏惧自己有过的一切机缘。在《这些人,那些事》的序言里,他写了四个算命的人对他人生的预测,那种将生命中未知的领域交给一个陌生人来排序的信任,其实是对未知生活的畏惧。想借着别人的提醒,来避开不必要的沉重。
他不是一个被恩宠过的孩子,幼小时的记忆是贫穷和尴尬。在《只想和你接近》中,给受伤的父亲剪完指甲后,作为奖励,父亲领他看的电影竟然在他的脑子里储存了二十年。而电影《恋恋风尘》中,醉酒后的父亲给“阿远”的那块手表,也是对吴念真自己生活的抄袭。《心意》里写到的那支“俾斯麦”牌钢笔,就是父亲醉酒后仍然没忘记买给他的礼物。
村庄里的人真的很多,让我们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赞美吴念真有写作才华的,竟然是将吴念真父亲抓去派出所的警察。这个驻在他们村子里的警察很胖,当时吴念真的父亲喜欢赌钱,赌得昏天暗地,不顾家里。吴念真将此事写到了日记里,被老师看到,老师建议吴念真写一封信来举报自己的父亲。可以想象吴念真写这封信的情景,我想到了张爱玲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用英文写信给报馆,骂自己父亲的情景。写信的结果,除了换来信的曝光率(村子里大多数人都来参观这封举报信)以外,还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吊起来打了一顿。而关于这个警察的模样,吴念真写到了电影《多桑》的剧本里。直到多年以后,吴念真出名,那警察还记着他。
这些人还有很多,整天嘻嘻哈哈从不调皮捣蛋的傻子阿荣,最后却成了抢劫犯;给弟弟买大一号衣服的阿旺;背九九乘法表的老鼠仔;做过妓女,偷偷来求吴念真给她的哥哥写信借钱的阿英;帮着吴念真和战友小包证明清白的店铺女孩阿媛;只是孤独得厉害在深夜抱了一个女孩便被抓到监狱里的“强奸未遂犯”……
这些普通的人,或温暖,或滞重,或忧伤,或单纯,却一个个泛着尘世的体温,让我们在合上书本的瞬间,湿润眼睛。有一个读者在赞美吴念真的时候,说,我最讨厌煽情,可是,却在读吴念真的时候泪流满面。
越是简单内敛的感情,越容易产生共鸣。吴念真的文章像极了一曲舒缓又温暖的钢琴曲,中间有转折的音符,将我们共同的记忆打开。翻开这些日常的人和事,我觉得像进入了一个储满秘密的地下室,而吴念真正是配钥匙的那个人。
(摘自《南岛视界》2014年第5期)